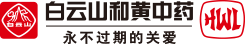新金融觀察報:OTC廣告禁令之爭
一場圍繞OTC藥品廣告禁令的各方角力,仍在進行。從傳聞乍起時的慌亂、到研討會上集體反對、再到現今多數觀望,OTC藥企的姿態呈現出過山車之勢。
這一情形仿佛昨日重現,10余年前,處方藥被禁止在大眾媒體上投放廣告,在業界同樣喧囂一片,但最終得以實行。
不可否認的是OTC藥品多帶有大眾消費品的屬性,在傳播上與大眾媒體緊密相連。江中藥業(20.20,0.13,0.65%)、哈藥股份(5.85,-0.01,-0.17%)、云南白藥(63.00,-0.15,-0.24%)、華潤三九(23.70,0.21,0.89%)等OTC藥企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其在大眾媒體上連番轟炸的廣告功不可沒。
但不論禁令實行與否,藥企曾經情有獨鐘的傳統媒體及營銷生態正在面臨新的改變,而這也對其營銷策略提出新的挑戰。
新金融記者
陳一昀 曹曉龍 北京報道
一場圍繞OTC藥品廣告禁令的各方角力,仍在進行。從傳聞乍起時的慌亂、到研討會上集體反對、再到現今多數觀望,OTC藥企的姿態呈現出過山車之勢。
這一情形仿佛昨日重現,10余年前,處方藥被禁止在大眾媒體上投放廣告,在業界同樣喧囂一片,但最終得以實行。
不可否認的是OTC藥品多帶有大眾消費品的屬性,在傳播上與大眾媒體緊密相連。江中藥業、哈藥股份、云南白藥、華潤三九等OTC藥企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其在大眾媒體上連番轟炸的廣告功不可沒。
但不論禁令實行與否,藥企曾經情有獨鐘的傳統媒體及營銷生態正在面臨新的改變,而這也對其營銷策略提出新的挑戰。
變數與觀望
10月11日,在南方一家以OTC產品為主的大型藥企的公司例會上,其市場部負責人就OTC藥品(即非處方藥)擬禁止在大眾媒體上發布廣告一事做了簡要說明,但并未展開來談。
事件源于9月27日,多家媒體報道稱SFDA(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簡稱)正在醞釀《藥品廣告審查辦法》的修訂稿,修訂方向為禁止OTC藥品在大眾媒體上發布廣告,只能在指定的專業媒體上發布廣告。
緊接著,修訂稿的首頁內容也被公布在微博上。
各界嘩然。
9月28日早上,康美藥業(16.26,0.01,0.06%)OTC事業部總經理李從選向新金融記者表示,OTC藥品廣告禁令會促使藥店自己的貼牌品種橫行,而做貼牌的都是小廠家,且藥店要的毛利高,藥品質量將難以保證,另外,OTC做品牌是有品牌溢價的,不能做了,也就很難成為全國品牌,藥企的發展和集中度提升將受到限制。
當天下午,關于這一修訂方向的研討會在北京如期召開。參會人員有三方,為SFDA、中國非處方藥物協會和近30家藥企。
據媒體報道以及中國非處方藥物協會工作人員回憶,在研討會上,藥企代表提出一些建議,SFDA做出回復:“但當時沒有得出結論,只是初步溝通。”中國非處方藥物協會工作人員向新金融記者表示,目前沒有一個定論,作為旁聽者,對于修訂稿的實施與否,他們也無法判斷。
但同時,該工作人員又認為,修訂稿不會草率出臺。就他的個人觀點而言,“政策出臺是不可避免的,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
事實上,對于禁令會否實施,業界有不同聲音。
資深醫藥廣告人、引力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醫藥事業部總經理劉澤輝(微博)在10月10日向新金融記者透露,關于OTC藥品在大眾媒體上的廣告,“據說有60%的禁播可能性。”
戲劇性的是,在同一天晚上8點前,另一位資深醫藥廣告人、北京思享廣告有限公司總經理李衛民通過微博公開表示:剛聽到內部消息,因出臺后遭到巨大反對聲音和大量質疑,關于不許OTC品牌在大眾媒體打廣告的動議已經暫停了。
為此,新金融記者致電SFDA新聞處,其工作人員表示,他們還沒有接到修訂稿暫停的消息,關于《藥品廣告審查辦法》,目前還在征求各方意見中,沒有最新進展。
SFDA曾對媒體進行書面回復,稱修訂稿是“為嚴格藥品廣告監管,規范藥品廣告發布,制止利用違法藥品廣告損害廣大消費者利益的行為。”并在研討會上披露,我國的違法藥品廣告包括假藥和超適應癥宣傳情況十分猖獗,嚴重違法廣告率已高達58.2%。
在新金融記者采訪過程中,盡管多數業內人士表示出對此數據的懷疑,但都不得不承認已查處的違法藥品廣告次數之多。
西安漢豐藥業有限責任公司市場總監孫輝認為,出現這個動向,主要是這些年OTC廣告夸大功能及虛假宣傳太多,僅2012年第一期曝光就有3萬余期,藥品及廣告質量良莠不齊、魚龍混雜。因虛假廣告誤導,每年約有250萬人“吃錯藥”,一般來講,大品牌藥企的產品更有保證。
劉澤輝表示:“違法廣告不過是個幌子,最關鍵是想讓OTC藥品降價。不是廣告降價,是藥品降價。”他表示,OTC藥品廣告費用一般會有5%~10%轉嫁到藥品價格中。
但廣東良方藥業有限公司總裁柯華松表示出不同看法,雖然廣告會增加OTC藥品的營銷成本,但是很多OTC藥品的價格是發改委和物價局在管理,比如基本藥物板藍根的零售價,國家已經固定了,即便投放廣告也不能超出這個價格。
事實上,早在9月24日,劉澤輝便在微博中提及有關修訂稿的疑惑,并稱已下發討論,OTC協會(即中國非處方藥物協會)正邀請30余家企業來京協商對策,并積極與相關部門溝通中。
幾天后媒體的報道、研討會的召開,致使修訂稿的討論與爭議急劇沸騰,而隨后開始的8天小長假又使爭議熱度有所緩和,在經歷了研討會上激烈爭辯的藥企們,現在大都選擇沉默,對事件呈現出觀望的狀態。
據媒體報道,在研討會上首位發言的是西安楊森的媒介總監高峰。而在截稿前第3天,新金融記者向西安楊森的公關部負責人任可可詢問時,她表示公司目前沒有對這方面的回應。
盡管此前曾有人表示修訂稿通過的可能性較大,但多數藥企在擔憂的同時,也表現出相對樂觀的態度,除在研討會中向SFDA積極爭取外,并沒有大刀闊斧的舉動。
上述南方一家大型藥企的相關負責人也對新金融記者表示,他們正在關注事態的發展,但目前還是按照正常的規劃來執行,至于備選方案,還沒有成型。
事實上,關于禁止OTC藥品在大眾媒體上發布廣告的建議,早在多年前就已被提出。
為了加強處方藥的管理、規范非處方藥的監管,SFDA于1999年6月發布《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辦法》(試行),并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該《辦法》第十二條明確規定,處方藥只準在專業性醫藥報刊進行廣告宣傳,非處方藥經審批可以在大眾傳播媒介進行廣告宣傳。
據一位從事醫藥市場推廣20余年的業內人士透露,在討論禁止處方藥做大眾媒體廣告的時候,就有人提出來一并禁止OTC藥品在大眾媒體上發布廣告,“當時通過了處方藥的決議,而沒有通過OTC藥品的。”
究其原因,該業內人士分析稱,經過討論,認為OTC藥品廣告還有一定的市場需求,“這是一個利益角力的過程。”
在之后的許多年里,“一直有人提,但聲音不大,這次是聲音比較大了,所以才動真格了。”該業內人士說。
從“兩片”到“哈藥模式”
通常來講,OTC藥品廣告的發布渠道有電視臺、電臺、平面媒體,還有新媒體等。其中以電視廣告投放為主。
安邦咨詢醫藥行業分析師夏慶表示,由于老百姓可以自由選擇OTC藥品,為了提高銷量和品牌知名度,OTC藥企們心甘情愿地花重金在各大媒體上發布廣告,這已是司空見慣的營銷方式。
而OTC藥品廣告登上國內電視熒屏已經20多年。
中國健康教育中心工作人員吳窮告訴新金融記者,中美史克(中美天津史克制藥有限公司的簡稱)的“兩片”打開了國內OTC藥品電視廣告的先河。
公開資料顯示,1987年,中美史克將OTC藥品史克腸蟲清引進中國市場,并在國人對于廣告稍顯陌生的情況下,將史克腸蟲清稱為“兩片”,在中央電視臺以及其他媒體發布廣告。有記載稱,那段時間,說“兩片”幾乎成為人們街頭巷尾見面的口頭語。中美史克一炮打響,“兩片”賣得火爆。
趁著史克腸蟲清廣告的火熱,一些經濟實力較弱的小型藥企搭上了“順風車”。“小企業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用了一種我們認為不太道德的做法。”吳窮對新金融記者說,有些小企業將產品名稱改為月易蟲清,乍看像是“腸蟲清”,“不能說它是假藥”,但這樣的做法實在不算厚道,可是“這樣的企業很多”。
繼中美史克的“兩片”之后,接連以電視廣告形式出現的是西安楊森的息斯敏、達克寧、嗎丁啉等。吳窮表示,這些都屬于第一批以電視廣告方式出現的OTC藥品。
一份公開的《1991年西安楊森廣告綜合調查報告》中顯示,當時,息斯敏的患者用藥率為36.6%,達克寧為35.4%。息斯敏和達克寧在市場開拓上獲得明顯成功,不僅為消費者接受,而且已經在同類藥品中上升為主要地位,開始超過傳統藥品。
而廣告在提高二者的產品知名度和實際銷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兩種藥品的產品知名度在當時分別達到44.4%和36.1%。
但是隨后的幾年,抗過敏藥息斯敏被陸續發現產生不良反應,最終因飽受爭議在部分國家和地區退市。其電視廣告也隨之消失。
據吳窮介紹,一般來講主動停播電視廣告的企業有幾種情況,一是企業認為市場已經被滿足;另一種情況則是隨電視廣告費用不斷上漲,性價比不合算;還有種比較極端的例子則是產品退市。
在OTC藥品廣告逐漸變得熱門的時候,1998年,國內首個處方藥電視廣告出現,是輝瑞公司的活絡喜。但只是“曇花一現”。處方藥很快被禁止在大眾媒體上發布廣告。
按照《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辦法》(試行),消費者有權自主選購非處方藥,而處方藥必須憑執業醫師或執業助理醫師處方才可調配、購買和使用。
非處方藥直接面對消費者,而處方藥的推廣需要醫師這座橋梁,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二者的傳播渠道會有所不同。
OTC藥品電視廣告的發展并沒有受到處方藥廣告禁令的影響,而是愈發高漲。在赫赫有名的“哈藥模式”之前,濟南三株福爾制藥有限公司生產的三株口服液曾因廣告投放而“名震一時”。
嚴格意義上講,三株口服液算不上OTC藥品,而是保健食品。之所以提及它,是因為在1995年,廣東省衛生廳曾發布《關于吊銷三株口服液藥品廣告批準文號的通知》,稱濟南三株保健品廠在《珠江經濟信息報》上刊登的藥品廣告,超越了《藥品廣告審批表》審批的內容。
虛假廣告宣傳,這是三株口服液最終走向失敗的開始。即便在此之前,三株從未吝嗇過對于大眾媒體廣告的投入,并因此創下了了不起的銷售業績。
在這之后,“哈藥模式”如期到來。
所謂“哈藥模式”,業界給出過多種定義,有些表述為見縫插針式的廣告投放與銷售渠道,還有些稱為巨額投入,大面積轟炸等諸如此類。
可以說,在“哈藥模式”盛行時,只要打開電視,轉動頻道,幾分鐘之內,就會看到哈藥集團的藥品廣告,比如蓋中蓋、嚴迪、三精葡萄糖酸鈣、三精葡萄糖酸鋅,包括哈爾濱制藥六廠、哈爾濱制藥三廠的品牌字眼等時刻沖擊著人們的視聽。
吳窮認為,正是從“哈藥模式”開始,“OTC藥品廣告變成了純功利的形式,沒有藝術價值、沒有美感,只是不斷地強化品牌,一遍又一遍地擾亂視聽,通過電視廣告給老百姓強灌信息。”
他還表示,早期的OTC藥品廣告含有自我藥療的信息,有一種健康知識的傳遞意識,而后來的“哈藥模式”是純粹的品牌提示。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轟炸式的廣告投放帶給哈藥集團十分可觀的回報率。據了解,1996年,哈爾濱制藥六廠的銷售額為1.3億元,1998年增長為2.3億元,而1999年暴增到10億元,2000年再次翻番到20億元。哈藥集團同年的銷售額也由38億元變成58億元。
于是,不少OTC藥企競相效仿。“哈藥模式”沿用至今。
但隨著2001年SFDA停止受理大眾媒介部分處方藥廣告有關品種、包括抗生素類處方藥的文件公布,有中國重點抗生素生產基地之稱的哈藥集團頗受打擊。
“點”與“面”的關系
蘿卜青菜,各有所愛。并非所有OTC藥企都青睞于“哈藥模式”。
2004年,在合資藥企廣州白云山和記黃埔中藥有限公司(下稱白云山和黃)成立之前,張平(化名)就已加入白云山和黃的前身廣州白云山中藥廠,并長期負責省級OTC市場推廣。
白云山和黃的OTC產品比重占到90%以上,有板藍根顆粒、口炎清顆粒、穿心蓮片、六味地黃丸、止咳枇杷顆粒等。
據張平介紹,當時,白云山和黃在全國各地均設有辦事處,全國近2000人的OTC營銷隊伍,三級渠道布局比較扎實。鑒于此,白云山和黃在推廣第二梯隊產品時,并非依靠電視廣告進行轟炸,而是憑借已有的營銷網絡,有選擇性地在大眾媒體上發布廣告,與“地面”部隊有機結合,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在2003年非典時期,板藍根暢銷,而廣州白云山中藥廠堅持其板藍根產品不漲價。在這一事件營銷過程中,尤其與許多借機漲價的板藍根廠家相比,白云山和黃的口碑和美譽度得到消費者的肯定。
這種事件營銷的方式直接傳承到合資之后的白云山和黃身上。2005年,白云山和黃推出“家庭過期藥品回收(免費更換)機制”,打著全球首創的旗號,持續近6個月的時間里,在全國近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開展活動。
時至今日,白云山和黃仍在堅持這種事件營銷的方式。“家庭過期藥品回收(免費更換)機制”進行到今年,已經是第八屆了。
“花小錢、辦大事,這是它的高明之處。”張平評價說,純粹的廣告顯得比較生硬,相比之下,將訴求融入事件營銷中,消費者會更有好感、更加認同。
同時,白云山和黃一直非常注重企業品牌建設,如白云山品牌價值估算、成立現代中藥博物館——神農草堂,統籌在全國性電視、報紙等大眾媒體上做品牌類的廣告。
據白云山和黃有關負責人表示,公司目前的市場推廣形式,在大眾媒體上投放廣告的比例占到50%~60%,除此之外,還涉及一些地面活動,包括事件營銷等。“相當于地面與廣告的相結合,既有‘點’的涉及,又有‘面’的覆蓋。”
白云山和黃在全國各地的辦事處,相當于“點”,而在全國性媒體上的廣告投放,相當于“面”。就二者的回報率來看,“消費者教育這方面,‘面’的教育沒有那么深入,但范圍比較廣,而‘點’的教育正好相反。”該負責人說。
李從選也表示,廣告與地面的推廣形式是相輔相成的,“沒辦法說哪個效果更好,因為只打廣告,終端沒人跟蹤,就不能落地;相反,光有落地,空中沒有支撐的話,消費者或連鎖藥店也不信任。”
就電視廣告而言,一般有30秒、15秒的廣告和5秒的標版廣告之分,能夠承載的信息量較小,“它可以讓老百姓知道它的品牌,卻不了解品牌背后的故事。”吳窮對新金融記者說。
業界看來,市場推廣費用一般占到藥品銷售額的10%~15%,包括廣告投入、給醫師開會、對藥店店員培訓等。
夏慶告訴新金融記者,年報顯示,一些知名OTC藥企每年投入的廣告宣傳費用動輒億元以上,甚至有的公司年報披露廣告的拉動效應很好地助推了公司業績的增長。2011年,云南白藥的廣告宣傳費用為5.08億元,占主營業務收入的4.5%;哈藥股份的廣告宣傳費用為4.48億元,占主營業務收入的3.4%;仁和藥業(6.86,0.04,0.59%)的廣告宣傳費用為1.33億元,占主營業務收入的6.0%。
據吳窮介紹,OTC藥品從在大眾媒體上發布廣告,到體現在銷售額上,速度很快。“一般是鋪貨鋪好后,再投放廣告,有時一周之內就會起效,但是它的生命周期很短,藥企必須要維持一個高額的投入,才能得到一個高額的產出,尾效應較短。”
吳窮舉了一個例子,“比如說一款OTC藥品,投放了3年的廣告,第4年突然不投了,那有可能從第4年開始,一個月之后,它的銷量急劇下降。”
上述白云山和黃有關負責人表示,公司這兩年的廣告費用基本持平,但廣告價格每年都在漲,所以從投放量上來說是有所下降的。相應地,其市場推廣費用在銷售額中所占比例降低為7%左右。另外,由于原材料及人工等各項成本的上漲,目前白云山和黃在全國的OTC營銷隊伍已縮減為1000人左右。
市場推廣費用的降低不見得是件壞事。吳窮分析說,OTC藥品隨著廣告投放時間的增長,知名度也在變高。藥企在推廣一個品牌的時候,往往初期的幾次,大家的印象不會很深刻,而堅持投放三個月或者一年以上,人們自然會有所熟悉。這是一個維持量,而不是沖擊量。
“很多藥企投放廣告,剛開始時,每天投放3次,3個月后,變成1天1次,半年后,變成一周兩次,一年后,維持一周或兩周投放一次的頻率,逐步遞減下來。”吳窮說,到了后期,知名度得到認可后,藥企會轉移部分精力到終端上來。
在采訪過程中,部分藥企向新金融記者傳達了這種意愿。白云山和黃有關負責人表示:“如果把‘面’取消了,就只能做‘點’了。”李從選也表示,“如果禁令實施,只有在終端加大投入力度了。”
而在加強終端的同時,藥企也在擔心成本的提高。“品牌產品是全國性覆蓋的,而社區里面的健康教育會議,可能只有幾十個消費者,累積起來的費用會更高。”白云山和黃有關負責人說。
有人建議說如果OTC藥品廣告禁令通過,藥企可以選擇投放品牌形象廣告。但吳窮認為,這只是目前缺少學術價值、趨于品牌提示的OTC藥品廣告的一個變種。相較于表達直白的“哈藥模式”,早期充滿學術韻味的藥品廣告或許更加含蓄。
而孫輝認為,OTC藥品本身就具有廣告推廣的合理性,若簡單地禁止OTC藥品廣告,對一些多年來具有美譽度、影響力的企業確實不公,如何在今后倡導合理安全用藥、如何促進和評估廣告正面效應,以及如何建立有序的競爭環境都是我們應該思考的。
在學術營銷與廣告營銷的選擇上,或許二者的結合,才是OTC藥品廣告的最佳歸屬。